德国汉学家看中国文学: 想要理解中国的人必须要阅读
导读: 在西方,人们几乎不了解中国文学,或者是只在政治和道德的考虑下才阅读中国文学,我们是时候拓展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视野了。
正文
1
2017 年是一个并不缺乏重大事件的时期,在回顾这一年时,有一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是美国总统的两个孙子。这两个孩子站在他们的父母Ivanka Trump和Jared Kushner中间,为中国国家领导演唱了一首中文歌曲。Joseph有些腼腆地靠在他父亲的腿上,但5岁的Arabella在这一天却游刃有余。不久之前她已经用她标致的幼儿汉语叫着“习爷爷”欢迎了中国国家领导。

这张照片拍摄于特朗普弗洛里达州私人住宅的接待室中,这里有着金质的壁板、奶油色的沙发和旋转的石柱,一切看上去像是皇宫一般,仿佛根本不是在西方最早的民主国家。在这张照片的左边,站着有着橙金色头发的美国总统,他微笑着,却没有站在中心,相反,照片中间站着的是国家领导的夫人彭麻麻,她的丈夫在她身旁,一起满脸微笑地看着这两个孩子。这时也许不止一个观察员在心里打了个寒颤,似乎这一幕体现了地缘政治的情势变化:或许西方的时代即将在Mar-a-Lago走向结束。
(Mar-a-Lago: 海湖庄园,美国弗洛里达州的一处美国国家历史名胜,1985年被特朗普收购。特朗普一家人在庄园内有私人住宅区和活动区域,不对外开放。特朗普将海湖庄园称为自己的南部白宫,上任后多次在海湖海湖庄园接待外国宾客,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领导人。)
当下的形势冲击使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环境。有些人曾经相信,在这个受不断扩张的“持续现在”所影响的时代,未来会越来越少,然而这个观点在特朗普执政大约18个月后看起来几乎是幼稚的:未来存在,未来仅会突然出现在其他地方,并且在瞬间发生,是的,或许正好出现在中国:自由贸易、经济改革、人工智能、太空探索和超现代主义。 那些曾经处于边缘位置的事物如今正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挤向一个空的中心。只是,这样发起的多边大国合作在文化层面意味着什么?什么将在全球的核心空间发生变化?仔细听过Arabella唱的中文歌(顺便一提这首歌叫茉莉花)的人也应该思考,伴随着汉语时代在全球文学中的来临,什么又将发生变化?
2
关于中国的文章已经写了如此之多,以致于有关中国的文章写作难度已经是一个被多次讨论的问题。这种希望了解中国的想法经常使人产生一些误解:中国是激进的异类、是反欧洲的(Leibniz)、 中国还处于原始状态、中国是让人向往的地方。如果有人听到“中国”这个词想到的一直都是Jorge Luis Borge虚构的中国百科全书,只能说他根本不了解外国。然而,在欧洲大西洋的世界谁能完全了解像杜甫、苏东坡、曹雪芹,茅盾或者张爱玲这些中国的名字?面对如此多的文化盲点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了解中国呢?!
事实上,当代汉语文学作品像一个耀眼的神秘物种一样变化多端,并且声称自己在全球文学市场上日趋成功,这也是因为汉语文学作品无论如何必须代表世界一隅13.79亿的人(非常紧张,渴望成功,历经磨练)。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有很多东西需要修改,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或马来西亚的文学一直被谴责为一种封闭独立的存在,被关在所谓的“中国笼子”之中(Eva Lüdi Kong, 《西游记》译者),如今这个笼子已经被打开一半了,一则三月末新鲜出炉的报导显示: 亚马逊公开表示将花10亿美元购买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三体系列丛书的版权,以此来创作《权力的游戏》 的衍生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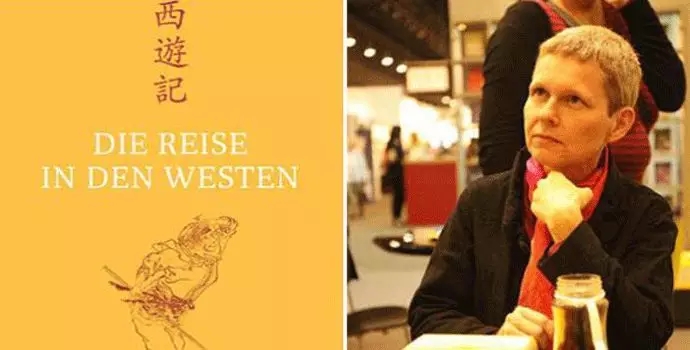
Eva Lüdi Kong
John Updike(美国长短篇小说家,诗人)在评价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时直接说,中国的小说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维多利亚的全盛时期”。无论他怎么认为,这样的评论都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意味:好像美国的作家们无法想象,有人能在没听说过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或亨利·詹姆斯的情况下写出巨著。有趣的是2012年莫言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简要地向William Faulkner (美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和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百年孤独》)表达了敬意,他们赋予了他构建“高密乡”这一文学领地的灵感,这是他文学作品的核心。 但是他并没有认真全面地读过他们的作品,显然,本土叙事传统的影响才更具决定性。为什么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要使用和自己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模式来创作呢?
中国是非常多元的
直到今天,相比于高度精细化、医疗保障健全、注重生活方式实践的社会形态,乡村生活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要贴近得多。如果我们将搬迁到中国生活,那么也有很多我们难以融入的事情:农民们乐于在Qzone社交平台上和当地的党委书记进行交流;党委书记必须时常重读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佛教的地狱或者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在新年(或是去赌城澳门度小长假时)会穿红色的内衣,因为这样会带来好运;此外他们还会读蒲松龄(1640—1715)的志怪小说;最后,在淘宝贸易方面(有着6.5亿潜在互联网用户)农民与典型欧洲国家的居民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中国是非常混杂的,是新历史的,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现代与前现代的多元混合。香奈儿(Chanel)和古驰(Gucci)被放在社会主义美学(民间木版画)旁兜售,这里人们的生活是非常物质主义的,但同时也追寻生活的意义和宗教的深度。仅在过去的几年,政治环境以一种另人惊骇的速度恶化了,日益严格的绝对治理替代了从前的自由(据说人脸识别软件天网可以在瞬间从十亿人中捕捉出一个人)。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截然不同的世界呢?
3
莫言和余华是当代中国文学在国际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展示了当今中国文学意识的很多方面。他们两人都亲身经历了文革以及毛泽东极权主义下所有其他的过激行为。他们的小说作品来源于对性和语言解放的坚定意愿:他们用炽热的想象力和一种野生的(通常是孩子般的)语言拼写出创伤,这些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村居民)在这场共产主义的革命之前、之中和之后所遭受的创伤。
在八十年代,他们的作品让许多读者感到解脱,因为这是文学第一次被用来对抗执政党注定的沉默,用直白刺目的语句来讲述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莫言的小说如《檀香刑》(2001;德语版2009)和《蛙》(2009;德语版2013)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余华的当代中国狂野世界的肖像——小说《兄弟》(2005/2006;德语版2009),通过很多暴力场景的描写表现出背后对受害者深切的同情:比如宋钢和李光头,两个异父兄弟,他们沉浸在痛苦中不愿意辨认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父亲的尸体,而是寻求邻居的答案来逃避现实,这个故事带着许多高度还原的荒谬细节,也有着大胆而动人的叙述。

莫言
然而西方评论界对这些书也产生了一些反对倾向。总是情绪过于饱满地悲痛,缺乏心理深度,粗俗的、对女性怀有敌意的笑话。尤其是在当今,西方的文学评论经常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考察:很快就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一个来自中国的作家在捍卫他的政权。 因此莫言受到了谴责,他的小说里“愚蠢的喧闹”事实上只是一种为了掩盖压抑残酷现实的方法。好的小说必须去描述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不能有更多的选择吗?如果今天有阎连科这样的人继续专注于讽刺文学的创作并且在他伟大的复调小说《四书》(2011;德语版2017)中比莫言更为真实地描写劳改所和饥荒的现实的话,他一定会因此对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产生关键作用。
然而我们应该警惕一点:我们肯定的、应当的道德反应,就一定是事实吗?当然,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有这种让人恼火的做法,即通过提及自己政府的不足来减弱对外国政府的批评。此外,个人的感知能力也容易被这样或那样的东方主义侵蚀。但是,对于如今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家来说,道德上的愤怒和无条件的团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开放以面对当下让人困惑的混乱!但是,中国文学的国际接受度总是陷入一种双重束缚之中:道德上的自我确信和对其他广阔的文学领域的极度认知匮乏。那么,究竟是应该揭露真相还是应该讲故事呢?
正是因为我们的目光不可抗拒地被文革所吸引,所以很少关注审美与政治进一步的可能性。例如香港作家陈冠中的最新小说《建丰二年》(2015):这部架空历史的小说描写了中国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假设毛泽东在内战中被蒋介石打败。相比于持不同政见的最新书籍,我们或许能从这本细节丰富的小说里了解到中国更多可能的未来。只是这需要一点耐心:这本书暂时还没有德语译本,书籍从世界的另一端传到我们这里往往会延迟几十年的时间。毕竟,来自香港的大师金庸所创作的奇幻小说不仅仅是奇幻,他的书终于在西方世界也取得了成功(射雕英雄传英译版A Hero Born,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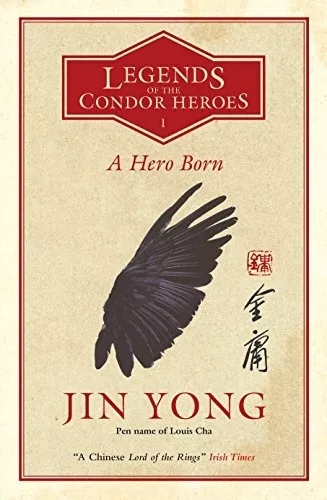
射雕英雄传英译版 A Hero is Born
4
中国当前的文学期刊让人光是看上一眼就非常沮丧:《收获》文学双月刊、《人民文学》、《文学评论》——因为所有的期刊都很官方,人们不是在纯粹地讨论文学,相反,人们常常用已出版作品的文字数量来介绍青年女作家们,在会议报告中经常提及的也是“国家复兴”(一些读者可能早已迁移到网络上,例如在豆瓣的相关网页上)。
然而,最近余华在文学杂志《收获》上讲了两个笑话,一个是关于中国人的,一个是关于法国人的。首先是中国人的笑话:一个拿着长竹竿的男人站在城门前,无论是竖着还是横着都不能让竹竿穿过城门的开口。一位路过的老人说,他虽然不是圣贤,但是可以给这个拿着竹竿的人一个建议:这个男人应该把竹竿分成两部分,然后就肯定能穿过城门。接下来是法国人的笑话: 一个卡车司机想开着他的卡车从一座桥下通过,但是对于这座桥的桥拱来说,卡车太高了。这时候走过来一个路人说:“我有一个想法:你为什么不把车轮卸下来呢?这样你的车肯定可以通过了。”这个中国的笑话起源于17世纪,法国的笑话则来自于我们当下混杂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笑了。中国作家声称,两个笑话都是关于愚蠢的,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余华当然是用中文为中国的读者写了这个笑话,从共性来说却是如出一辙:您在欧洲听过中国笑话的可能性相当低,可能您不觉得这个笑话有什么特别有趣的,然而这个法国的笑话却立刻产生了效果。因此您欣赏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可能性远远高于您欣赏上文提到的蒲松龄的可能性。在当代,绝对的确定性已不复存在,只有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作为命运的力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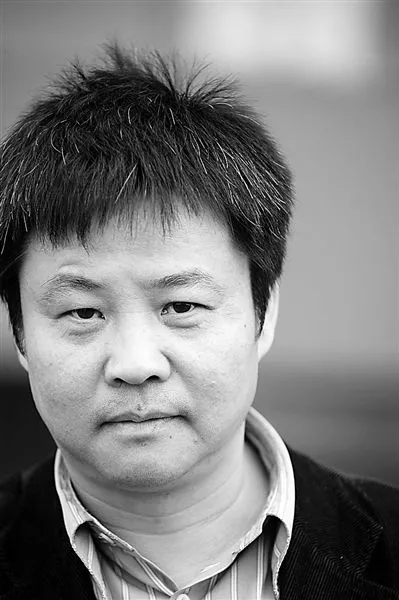
余华
社会现实给人的希望渺茫
人们阅读什么也是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力量的问题。在我们的地球上有很多国家有着很多的书,所有的国家都在争取得到关注并挤入世界文化认可的狭窄之门。当然,用必要的资金和广泛而紧密的机构组织网络有助于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事实上,所谓的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往往只是一个人们所宣称的。米兰昆德拉坚信,地理的距离将一篇文本从当地的背景环境中解放出来,这样才真正体现了一本小说的美学价值,这种想法也许还是太乐观了:如果异域文化的审美标准(例如来自中国的)和西方截然不同,那么就必须通过翻译或者编辑的技巧来削弱这种差异,因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理解文本。所以在全球流通的过程中不再引入美学要求极高的文本。
在这一点上,人们很乐意提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观;作品《亲和力》中的警告鲜有人知,作家Hans Christoph Buch在最近的一本论文集(Wege zur Weltliteratur, Klampen 2017)中提到:“在棕榈树下没有人会逍遥法外…”因为中国会越来越强势地维持他的全球领导力,可以预料到,这个国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将变得更加明显。他们会改变我们吗?
顺便一提,余华在一篇关于参观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文章中讲了两个笑话。任何曾经和中国人讨论过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及其对于当下意义的人都知道,这种对话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话语境中。这些对话经常以令人慌乱不安的沉默结束。人们愿意相信余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样反对恐怖和暴力——当然,中国的文学作品是无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现实分离的,现实让人感到希望渺茫。
5
毫无疑问:一旦习惯了Jonathan Franzen或者Joshua Cohen难以捉摸的、对愤怒的描写和深刻反思,就很容易对中国式肤浅又拙劣模仿的魔幻现实主义感到厌恶。总体而言,自我讽刺、世故且过分复杂的资产阶级主体很少见,而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小说文学的中心。
事实上,在地球的另一边确实也存在这样的小说。两位重要的中国资产阶级小说代表是张爱玲(Eileen Chang)和钱钟书,他们两者都和共产党指令粗暴的唯一性保持着距离,并代表着美学上的先进地位,正是由于他们立足于传统才能反映出新的社会差异。钱钟书的著名社会讽刺作品《围城》(1946/47;德文版1988)正等待着西方的重新发现。而张爱玲的优秀短篇小说《色·戒》(1978;德文版2008)尽管在由李安拍成电影后找到了新的读者,但是这个女作家的叙事作品从来没有被广泛地接受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损失,因为很少有描写上海和香港这样的大城市里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抒情记叙类小说。

张爱玲
即使是年轻的中国作家如格非(《江南三部曲》,2005-2012)或者毕飞宇(《推拿》,2008;德文版2016)都受到张爱玲精准的观察力的启发,有趣的是他们的榜样总是在汉语世界的边缘更具影响力,比如在香港和中国台湾。作者需要和后社会主义的核心保持更多的距离,从而能够用中文和文学的笔触大胆地描写白日梦式短暂爱情故事的偶然性,并且是以一种有赖于观察者感知深度和现代传记脆弱性的方式,正如张爱玲生命末年在一本关于她自己的精美照片集中所称颂的那样(《对照记》,1994)。诸如朱天心、李碧华、施叔青这些女作家深受其影响,而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甚至是后现代反传统主义骆以军(《西夏旅馆》,2008)或者董启章(《神》,2017)的作品中都有张爱玲的影子。尽管如此,中国文学领域在全球文学市场上依然被中国粗糙的男性化写作风格所主导。
6
一个中国作家的常见经历是,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且在一个荒芜的社会中再也找不到有意义的话语。格非在他三部曲的最后一卷(《春尽江南》,2015)中描写了一个年轻敏感的、读聂鲁达的诗人端午,他在八十年代一个命中注定的秋日里偷了他热恋女友的钱包,又在他们命中注定般的重逢的几个月后与她结婚。因此诗人没有死,而是作为一个贫穷的不切实际的丈夫,逃避到古典文学中继续活着。从旧的观念来说,格非获得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胜利,这对新中国的所有经济成就提出了质疑。去年四月,来自台北的26岁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杀也是一个相似的文化重演。在她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13岁的女主人公被她50岁的中文老师强奸了。林奕含在她死前不久的一个电视采访中透露,这个情节来自于她的亲身经历,然后她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语言阐释了她无条件的忠诚(这个老师通过柔弱的女性躯体的描述和古代字词来诱骗她,如怀才不遇,字面意思:“有才华但是缺乏运气”)。同样的文化民族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服务于共产党甚至有所增强,例如最近共产党让运动员和演员都参与到古典汉语的宣传中来。

格非
未来,汉语在西方世界仍将处于边缘地位。我们对于这种不同的文化形式要做的还有很多,从中反映出一种我们越来越不能忽视的新的自我意识。然而,现如今德国以及欧洲的自我认知早已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在一个想象中的民族文学里不再有自然的居住权(在德累斯顿或者Schnellroda也没有)。因此,此时此刻最适合考虑的是远东地区的情景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能提供哪些新的认知的可能性。世界文学也许在中国将变得更混乱、更富有想象力、更系统、更混杂并且更发散,因为它反映了更多人的命运。我们越面向世界阅读,就有越多的基础能够在这个新世界中感觉像在家一样。
出处: 《时代在线》
作者:Kai Marchal(德国汉学家)
发表时间: 2018年5月13号
此文由公益翻译使者提供
译者: Hanna
校对: 程荟矜
原文链接: https://www.zeit.de/kultur/literatur/2018-05/chinesische-zeitgenoessische-literatur-mo-yan-yu-hua/komplettansicht




